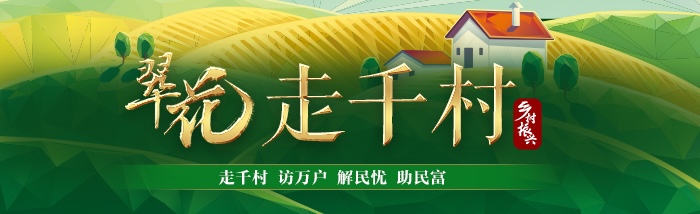
爐火正旺,熱騰騰的餃子出鍋啦。
大年初三,脫貧戶王可校換好了新衣服,下了輪椅,端坐在飯桌前。
雖是初三,飯菜卻不比年三十的簡(jiǎn)單:紅燒鯉魚、笨雞燉蘑菇、自制皮凍、青椒炒肉……
王可校開了瓶新酒,父子二人對(duì)坐小酌。
窗外,爆竹聲漸起,大紅燈籠將小小農(nóng)家院兒照得紅紅火火。
“兒子,現(xiàn)在咱村可不像從前了,能掙錢的路可多著呢!咱們有溫室大棚、有旅游、有豆包廠,很多年輕人都回來(lái)了,都掙著錢了……”酒半酣,王可校勸兒子回村發(fā)展,又讓媳婦把自己的小賬本找出來(lái)。
王可校是扶余市永平鄉(xiāng)九連山村的老黨員,曾在村里做過(guò)村干部,因?yàn)橄轮珰埣彩趧?dòng)能力,而一度陷入貧困。
王可校年輕時(shí)就有記賬的習(xí)慣,每年過(guò)年都要向媳婦和兒子公布上一年的收支賬目。
這是一個(gè)老式的筆記本,紅色的塑料皮有些破舊。在紅色賬本里,夾著一張A4紙,紙上寫著王可校剛剛統(tǒng)計(jì)的一年的收入:
土地入股合作社,得到種植產(chǎn)業(yè)分紅26000元;
公益崗2期,增加收入3000元;
低保發(fā)錢9000元;
合作醫(yī)療補(bǔ)助130元(全村都有);
殘疾人多項(xiàng)補(bǔ)助1920元;
兒子打工存錢20000元。
……
“在外打工不容易,又不比在村里掙得多,爸還是愿意讓你回村。”王可校端起酒杯一飲而盡。
兒子沒接話,拿起王可校的紅賬本看了起來(lái)。
“五一”村里分了粽子和咸鴨蛋;
“八月節(jié)”村里分了月餅;
春節(jié)村里給分了兩個(gè)大紅燈籠、四袋元宵,外加米、面、油……
“這賬,記得可夠細(xì)的啊!不愧是當(dāng)過(guò)村干部的。”兒子故意“戲謔”。
“好記性不如爛筆頭,一筆筆記清楚,心里有個(gè)數(shù)。別看我這腿壞了,腦袋好使著呢,看事情準(zhǔn)!”王可校告訴兒子,從2021年開始,扶余市開始深度謀劃九連山村的未來(lái)。2022年,九連山村黨支部領(lǐng)辦合作社便吸納了242戶483公頃土地入社,包括王可校在內(nèi)的村民,統(tǒng)統(tǒng)變成了股東。社員年終分紅總計(jì)760萬(wàn)元。
“村里剛剛公布的村集體資產(chǎn)已經(jīng)由2019年的672萬(wàn)元增長(zhǎng)到7227萬(wàn)元。我看,回村創(chuàng)業(yè)很有前景……”王可校看著兒子,眼里滿是期盼。








